韦东奕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并不是六代机
2024年12月26日,中国某新型飞机试飞成功,一时间舆论沸腾,众多网友和媒体纷纷将其称为“六代机”的雏形。尽管官方尚未明确表态,但有关这架新型战机的议论迅速升温。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没过多久,网络上竟然开始出现大量将该技术突破归功于“北大数学天才”韦东奕的说法。诸如“韦神你太牛了”、“大气层气流阻尼系数突破源自韦神成果”这样的言论在微博、短视频平台上疯狂传播,仿佛一夜之间,韦东奕就成了“六代机”背后的关键人物。
韦东奕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并不是六代机
但只要稍有常识或者具备一些科研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种浮夸炒作的舆论浪潮下,大量理性声音迅速站出来对这些无稽之谈予以驳斥。“韦东奕与六代机的关联,最多只能算在于流体力学的学科交集,他研究的方向是流体力学的基础方程——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但这与具体工程应用相距甚远。很多外行往往搞不清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巨大鸿沟。”
我之所以对韦东奕的研究方向有所了解,除了公开发表的论文信息外,还得益于一些从事科研工作的朋友们的介绍。比如我的几位数学和物理领域的同行——郭潇博士、周思怿博士、刘潇博士,他们都提到过韦东奕的专业方向。还有一位对韦东奕非常了解的前辈——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科普作家李淼教授。他曾担任“阿里达摩院青橙奖”评审,并亲自参与评定韦东奕在2021年获奖的过程,对他的研究方向极为熟悉。
韦东奕的研究集中在流体力学中的核心数学问题,主要聚焦于纳维-斯托克斯(Navier-Stokes)方程的解的性质。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是描述粘性流体运动的基本方程,在流体力学领域具有极高的理论地位,但距离战机设计或飞行性能提升的实际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轴对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与无粘阻尼问题》,被评为北京大学2018年度优秀博士论文。他在学术期刊《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上发表过研究文章,探讨特定条件下NS方程解的光滑性(即正则性)。
所谓“正则性”,通俗地说就是判断方程的解是否光滑、是否存在奇点。韦东奕的研究在于对一些特定数学条件下的NS方程解的行为作出严格证明,属于非常典型的数学理论工作。换句话说,他是在解数学的难题,而非解决飞机的阻力系数或者发动机推力问题。
此外,有人误解“流体力学研究成果可以提升飞行速度”,便牵强地把韦东奕的理论成果与“十马赫飞行”联系起来。这种推论完全是曲解,属于“望文生义式的臆想”。要知道,战机是否能实现10马赫,不取决于一个方程的理论解,而是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学、推进系统、热防护等一整套极其复杂的工程体系。
举一个简单例子,风扇的扇叶上常年积灰,并不会被风吹走,这是因为扇叶表面附近的空气基本是静止的。这就是粘性流体“贴壁效应”的直观体现,也是流体力学研究的一部分,但这跟如何让战斗机飞得更快并没有直接关系。类似的,还有人引用费曼的讲义解释风扇灰尘不动,是因为流体在接触固体表面时速度为零,这类现象说明了粘性阻尼的存在,而不是航空技术的突破点。
李淼教授曾指出,数学家在研究NS方程时主要关注定性问题,比如流体是否会形成奇异性、是否存在解,而物理学家更在意定量问题,即如何解出具体的流场分布或推算压力变化。在这一点上,数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韦东奕的工作,更多是站在理论巅峰上解一道世界难题,而不是研究如何制造高速飞行器。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误区是,有传言称韦东奕“曾经帮六位博士解决困扰他们四个月的问题”,后来也被本人及相关学界人士辟谣。事实是,韦东奕本人生活极为低调,不上社交媒体,也极少接受采访,关于他的传闻大多是网络“神话”出来的。而像“数学尽头是英语”这样荒唐的误解,也只是因为他的英文讲义被人断章取义,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中文。
2021年,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曾发布声明,呼吁社会给予青年学者一个安静专注的学术环境,避免过度关注和误读,文中就提到了韦东奕的情况。声明中写道:“韦东奕专注于数学世界,为人纯粹,生活简朴。”确实,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被网红化、符号化,更不应被营销号拿来博眼球。
今天我们依然敬佩韦东奕这样真正的学术天才,他的研究为数学乃至基础科学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但如果我们把他当成“六代机之父”,只会模糊科技界真正的分工与价值逻辑。这不仅误导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知,更是对他本人及整个学术环境的不尊重。
科学需要严谨,而不是神话;青年才俊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神化。希望大众理性看待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成果,也希望韦东奕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继续深耕,而不再被舆论裹挟。(责任编辑:张佳鑫)
精选推荐

特朗普怒火中烧,你们这些坏人!
2025-06-26 09:19:57
洪森:泰国总理要换人了 政坛暗流涌动
2025-06-26 16:34:02
记者:乌克兰的机会不多了 俄军优势扩大
2025-06-26 10:12:01
罕见!英国航母F-35B战机滞留印度超10天,英方担心技术泄密 引发两国媒体关注
2025-06-26 09:06:10
北约秘书长吕特就“严父说”作出澄清,特朗普:他当时深情地说“你是我的爸爸”
2025-06-26 09:22:35北约军费飙升至GDP的5%,坑的是谁?
2025-06-26 09:38:13
美媒:西班牙带头拒绝,北约联合宣言只好耍起文字游戏
2025-06-26 09:27:39
俄美元首有没有可能齐聚中国 抗战纪念活动或成契机
2025-06-26 09:16:5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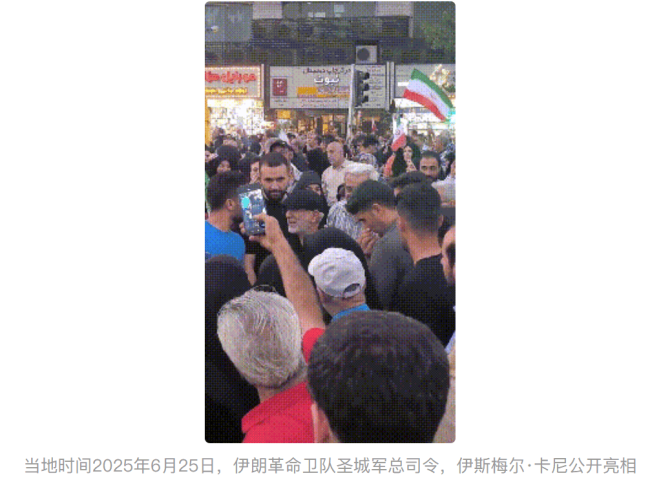
停战24小时,以色列迎来3个噩耗 伊朗小胜团结加强
2025-06-26 11:20:47
德国总理:没有理由批评美以 支持以色列行动
2025-06-26 14:4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