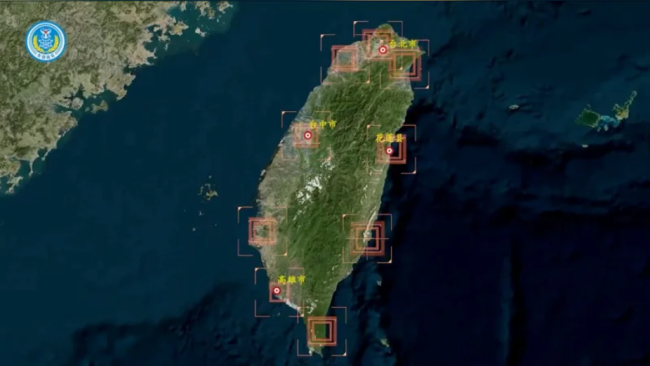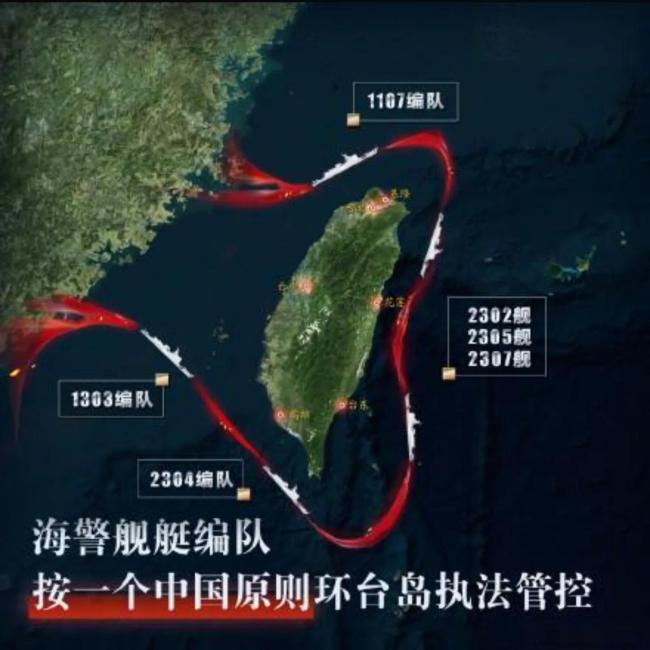德媒:美国也许不会回头了(2)
但随后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那位教父自己转身走了。奥巴马宣布要“重返亚洲”——这是针对竞争对手中国作出的新战略定位。他的继任者特朗普则宣布北约“过时了”。
2017年,彻头彻尾的跨大西洋主义者默克尔用安抚人心的话语表达一种充满焦虑的预感:“我们完全依赖别人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人们对德国可能很快就会在西方联盟中形单影只感到恐慌,这种情绪压倒了摆脱美国束缚的愿望。与此同时,大西洋联盟的几个创始国则在“美国优先”和“英国脱欧”的口号下堕入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揭示了欧洲对美国的依赖之深。没有美国带头援助,乌克兰就几乎难以生存。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德国该不该摆脱美国,而是能不能让美国人留在欧洲,以及怎么才能做到这点。
朔尔茨著名的“时代转折”演讲实质上就是在挽留美国。这位德国总理急忙撇清所有让人觉得德国要搭便车的嫌疑。
朔尔茨虽然很晚才信奉跨大西洋主义,态度却极为热忱。他在作重大决策前会与白宫协调,例如在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一事上。他有时实际上就躲在拜登身后。
这有着远超私人好感的深层原因。自冷战最危险的时期(即1948年和1958年的两次柏林危机)以来,德国对美国的依赖从没有像在面对俄罗斯的核威胁时表现得这么明显。俄罗斯的威胁使德国人再次意识到,美国的威慑力是德国安全政策的“人寿保险”。
现在,在基民盟胜选后,制定另一种外交政策方针的任务落到了将成为德国总理的默茨身上。但正如朔尔茨早年反美、后来却亲美,这种安排对默茨来说也不乏讽刺意味。默茨一直自视为跨大西洋主义者。他曾在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工作,任大西洋之桥协会主席多年。现在,默茨这个美国之友却不得不为德国制定另一套外交政策,以应对美国不是善意伙伴,抑或甚至是对手的那种极端情况。(责任编辑:许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