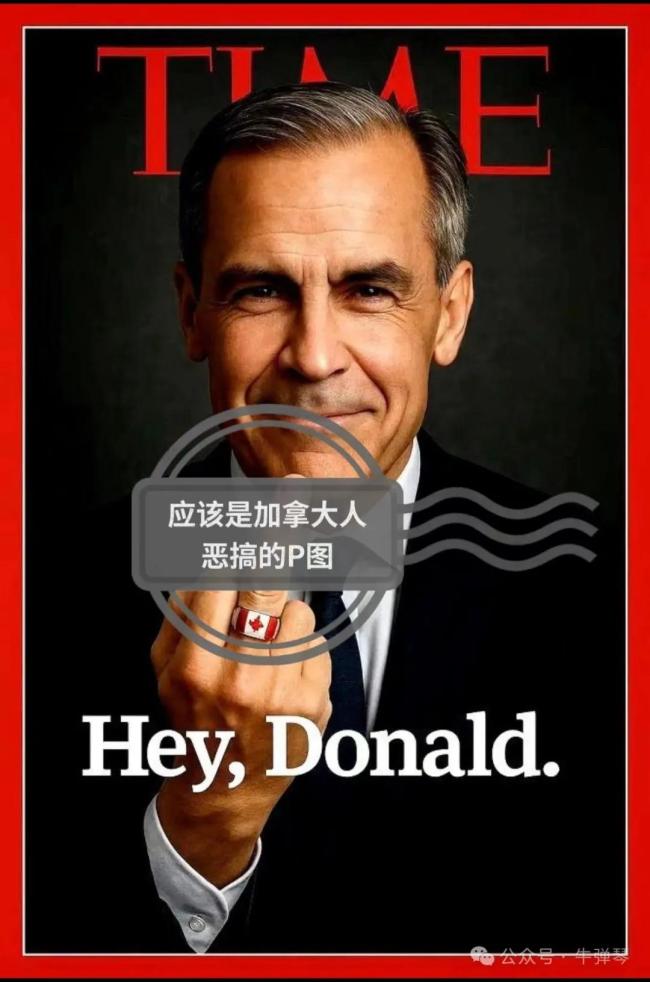托卡马克之冠:为何这次全球能有这么多声音谴责以色列?(4)
同样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整个西方社会,英、德、法、澳等许多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了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如伦敦已多次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甚至还有地铁司机用地铁广播带领车上乘客高呼声援巴勒斯坦的口号。
西方国家政府面临这种声援巴勒斯坦的汹涌民意,内部也极度撕裂:既有在相关问题上草木皆兵、对一切反以言论露头就打的,也有尝试突破舆论禁区、甚至公开对支持以色列的观点唱反调的。
前者的代表是德法等国。在德国,参加公开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可能会面临巨额罚款乃至驱逐出境的危险,诸如“解放巴勒斯坦”等在西方颇为流行的反以口号甚至被严厉封杀。
而后者的代表是爱尔兰和美国的部分政客。爱尔兰国会这段时间多次就巴以问题展开大规模辩论,而激烈声讨以色列、驳斥所谓以色列有权自卫的说法已经完全公开化了。甚至连美国都有国会议员公开批评以色列,部分社会名流在面对媒体要求其就巴以问题表态站队时,也阴阳怪气或东拉西扯不予回应。这在以往甚是难见。
于是,一个问题就显而易见地浮现出来:为何世界舆论在此次巴以冲突中,如此集中且广泛地出现了对巴勒斯坦的强烈声援?
在以往,由于美国在世界舆论场上的主导地位和对多种传媒渠道的垄断性把持,美国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力往往不局限于美国本土,而是具有超越国界范围的影响力,能够凭借着美国的传媒霸权倒灌进其它国家,塑造并影响他国舆论,形成“以美之是为是、以美之非为非”的局面。
而以色列在美国内部的有利地位也随着美国的影响力一并外溢到其它国家,成了一种跨国的道德体系。对以色列来说,则成为了一种政治特权,以色列可以凭借这种政治特权在国际上获得更广泛的行动自由。
精选推荐

美中情局发中文招募间谍被嘲 秘密机构的公开尴尬
2025-05-04 07:59:29
赵少康回应国民党遭全面追杀搜查 民进党下三滥手段
2025-05-04 11:53:04
刘宗义:黔驴技穷的印度,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2025-05-04 11:54:25
赖清德逃亡路线曝光:福建舰封死台岛东侧,美接应舰队掉头就跑
2025-05-04 11:58:45
胡锡进:特朗普又把澳大利亚丢了 反特朗普情绪持续发酵
2025-05-04 12:02:59
大V:俄军图-22M3轰炸机或大批退役 昔日“航母杀手”或将落幕
2025-05-04 07:46:2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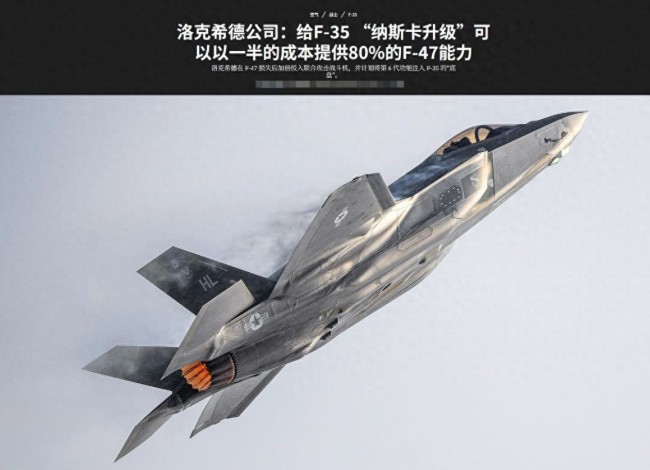
美国六代机B计划是美版“枭龙”吗 F-35改型能行吗?
2025-05-04 13:26:41
评论员:美军增兵南海目标很明确 制造双线压力
2025-05-04 13:24:46
媒体人谈美国大量回收硬盘换稀土 无牌可打的窘境
2025-05-04 19:06:31
越南一航班挂7700迫降高雄机场 紧急状况引发关注
2025-05-04 12: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