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为何又要对俄挥舞关税大棒 贸易外交再掀波澜
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他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这一举措虽然早有预期,但在中美两国乃至国际社会仍引发不小波澜。中美股市相继出现大幅下跌,投资者担忧中国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导致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甚至重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关税大战。
特朗普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自中美建交以来最为强硬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看起来不可理喻,但与其一贯风格相符。特朗普否定盟国、自由贸易及美国长期主导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轻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主张盟国支付“保护费用”。他在对俄、对朝、对华政策上明显与往届总统不同。特朗普的简单粗暴性格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构建的贸易和外交体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不确定性的担忧。
尽管特朗普政策受到国内政治精英、商界与舆论的牵制,且随着2018年中期选举的到来,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但预计其未来贸易和外交政策仍将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在美国优先原则下,特朗普追求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这决定了他的对外政策是收缩型的,更加重视周边。因此,特朗普会继续降低对全球治理的重视和投入,更重视双边关系,否定多边机制。他对中东、南亚、非洲缺乏系统性地区发展议程,采取限制和排斥难民的消极政策。在全球多边经贸安排上,他主张争取达成“更有利于美的交易”,破坏世界贸易体系开放性。
年内,特朗普政府将加快完成北美自贸区谈判和美韩自贸协定的修订谈判,并启动美英自贸谈判准备工作,研究与印太、非洲开展自贸谈判的可行性。面对日本主导的“TPP11国”进程加速,特朗普抛出了“考虑在TPP相关条款做出修改的前提下重返”的可能性,表明其致力于在“更好条件下”重订多边贸易协定的意愿。
由于特朗普未来一段时间政策重点在国内,在美国国内继续保持分裂的情况下,他在国际上制造分裂并主动“树敌”,以转移国内视线、凝聚民心,从而巩固其执政地位。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将继续关注核安全问题,并将反恐作为撬动地区地缘格局的工具,加强与中东、南亚盟友伙伴合作,遏制伊朗、制约巴基斯坦,扶植印度。此外,特朗普将继续推动其“新版亚太战略”,试图将贸易、安全等议题一揽子注入,实现经济与地缘的双重收益。
在大国关系上,美国内政治生态逐渐在美俄关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即使特朗普想要改善同俄罗斯关系,美俄在较长时期内仍然只能是若即若离。欧洲方面,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背道而驰,强调北约盟友分担责任削弱了盟友关系,双方在全球化、气候变化、难民等诸多问题上分歧重重。特朗普多次访欧、接见欧洲国家领导人,试图传递团结西方信号,但上述努力已被特朗普试图对欧盟征收高额关税的一纸声明击碎。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美国政府陆续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2018贸易政策日程和2017年报告》等文件,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随着特朗普决策团队中“国际主义派”的离职,“民族主义派”在决策中发挥主导性影响力,特朗普未来对外贸易、外交政策版图中,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将是“全面竞争、强制合作”。
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并获取优势将成为美国外交与贸易政策最主要的核心目标。然而,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竞争政策也受到不少限制。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令任何贸易战必然两败俱伤,历史上美方发动贸易战均未实现目标,反而恶化了战略竞争。特朗普此举已引发美国国内工商界的反对,认为这将伤及美国相关产业及消费者利益,无助于美国经济长远发展。
此外,中美在国际与全球事务上有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某些全球热点问题上,若缺少中国的合作,单靠美国及其盟友很难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美国缺乏遏制中国的手段,从主观看,美国自己也强调,竞争并非遏制,也并不必然是坏事,美方依然需要在全球事务上与中国合作。从客观看,特朗普政府缺乏遏制中国的资源与能力。特朗普“美国优先”不仅被美国战略界所不齿,别国也不愿为此买单;加上美国内经济不振、对外投资收缩,美国陷入“攘外必先安内”的窘境。
难以形成反华统一战线也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一个障碍。特朗普将安全与经济目标相互混淆,动摇其盟友体系。德、日、韩对美国逆差名列前茅,也是美国“公平贸易”的重要目标;特朗普政府要求他们更多分担军费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已遭这些盟友诟病。由此其战略与经济利益的相互冲突难以调和,这将掣肘其对华战略的实施。
特朗普对华政策最终将取决于其采取民族主义对外政策的内在冲动和制约条件两方面因素的博弈结果。但目前看,不利于中美合作的因素正在积聚。面对当前复杂的困局,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尽快实现会晤,再次发挥领导人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和引领作用。(责任编辑:张蕾 TT0001)
精选推荐

英国弹射座椅公司泄露了印巴空战战损“天机”?
2025-05-09 09:34:17
美国官员:巴基斯坦用歼-10击落印度阵风,没用F-16
2025-05-09 09:29:4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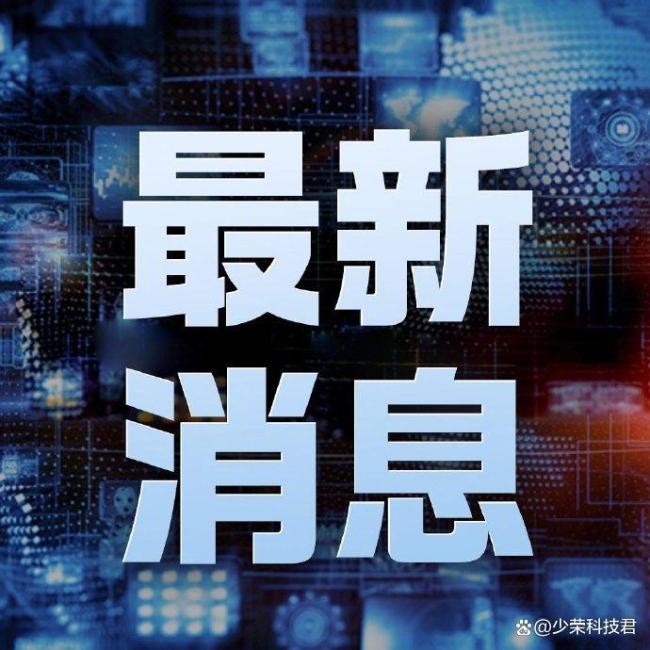
巴基斯坦:印巴冲突正进入死胡同 克什米尔再燃战火
2025-05-09 11:19:12
5月8日,世界发生了3件大事
2025-05-09 09:25:49
印“阵风”被击落,台退役将领质问“还能靠幻影吗”
2025-05-09 09:29:12
100多架飞机大战后,印巴局势怎么走?
2025-05-09 09:32:08
关税让美联储陷入“两难棋局” 观望成主基调
2025-05-09 11:41:25
专家:印巴空战结果让绿营陷入沉默 歼-10CE胜阵风引发反思
2025-05-09 07:42:32
普京与武契奇紧握双手:还好吗 武契奇绕道多国抵达莫斯科!
2025-05-09 14:00:01
印巴爆发近20年最严重冲突后,莫迪首次发声
2025-05-09 09:32:32











